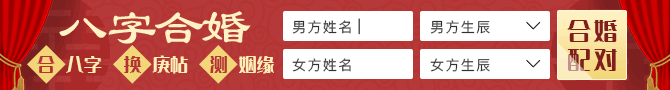揭秘什么是端公舞,有什么含义?
发布时间:2015年06月03日 10:30:26 作者:网络
端公舞又叫“扛神”,也叫“做枯斋”,被誉为楚文化的活化石。顾名思义,端公舞是被称为“端公”的人作歌起舞的一种歌舞形式。端公舞作为民间神秘文化,必然有其自己存在与形成的理由。那么什么是端公舞呢?端公舞又有神秘意义呢?快随小编来瞧瞧吧!
端公即“巫”,又称神汉,指施行巫术的人,一般指男性。端公舞虽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它更具有明显的楚文化遗风,端公的法术手段主要有五类:文书、诰咒、符讳、诀罡卦;巫术。分别源自汉字和官府的神化,源自民间佛道教中的巫术成分,源自西南少数民族信仰中的蓄盅人祀等,其性质相当于社会崇拜和自然崇拜。
端公舞传承楚国遗风--一群老人手执瓜锤、月斧和八卦旗,嘴里唱着古老的歌谣,在神秘、庄重的气氛中,请神赐福,据介绍,这种舞蹈是从2000多年前的古楚国流传下来的。楚国有崇巫尚神的风俗,端公舞源于楚国的宫廷舞,有人称之为巫舞。在山里人眼中,端公(即巫师)既能把神的意志下达给人,又能把人的愿望申诉于神,所以常常请端公做法事,祈福还愿。端公舞所用的道具中包括“钺斧刀”、师刀子(导旗)等。“钺斧刀”原是夏商两朝最高权力的象征。端公舞至少要7个人一齐表演,但目前只剩余无几,且都是住在偏僻山区的老人。
“端公舞”是鄂西北存于境内的楚时巫文化,是古代流传下来的巫教祭祀天神、地神、人鬼的歌舞,具有典型的楚宫廷文化遗风。
在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流域是古巴国的辖地。巴人崇巫尚武,《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代纣,前歌后舞也”,说的是巴师中有巫师参与做战。1976年,从城固县苏村出土的商朝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人、兽面具(人面23件、兽面25件)48件,从中也可看出端倪。这些面具应是早于“大傩仪”和“乡人傩”的巴人的“军傩”面具。
汉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巴、蜀、楚、秦,互相征伐而互有输赢,战后必有战俘、流民、奴隶,大量的移民迁入迁出,造成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楚灭巴蜀,而秦又灭楚,楚人项羽和刘邦又灭秦,而汉水上游终归成为巴楚古风的蕴藏地。
无论是巴楚还是秦蜀都给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上古时期的巫傩之风也就延至今日。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汉中人则习惯称其为“跳端公”。汉中的跳端公,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形式。
端公戏是由端公跳神时的歌舞发展而成的。地处大巴山深处的陕西镇巴,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端公戏得以长期保存,成为研究古代东方人体文化的活化石。端公戏,俗称“坛戏”,是一种巫师组班装旦抹丑、巫步神歌、踊踏欢唱的地方小戏。因其行头简单,一包袱可携,所以又叫打包袱。
端公戏的产生与陕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密切相关。汉水流域,南接巴蜀,东连楚土,风俗毕近,文化一体,巫觋之风颇盛。《汉书》、《宋书》、“地理志”都有“汉中之人,不甚趋利……好祀鬼神,尤多忌怨,崇奉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的记载。其“踏青药市之集”,实际就掌握在巫师道徒之手。他们白昼聚集售药,唱情咏事,招徕过往顾客;夜晚则受请作法,踏歌踊舞,娱神禳灾。他们在当地被混称为“马脚”,即天神马头驾前执事使者,负有神圣差遣、驱魔逐鬼的职责。
男巫习呼为“端公”,女觋惯唤为“神婆”。“端公”,为唐官职务,将巫师称为“端公”、“马脚”,可见他们在陕南人们心目中的神圣地位。群众每遇病痛灾疫,少请医生诊治,惯邀巫觋诉神。“愚民有病,初不延医而延巫,俗云端工,即古称担弓者也。正是这种巫觋之风,为端公戏的出现奠定了深厚的艺术根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端公戏实际是巫跳“神歌”与大筒子戏合流的产儿。它的发展大约经过了“坛戏”、“神歌”、筒子戏与职业班四个阶段。巫“跳坛戏”。萌生时期。一说春秋战国时的“桑田大巫”开其源。一说由两汉时期的“茅山祖师”张五郎创始。
“神歌”、“神戏”。早在屈原时代,楚汉之地喜作神鬼之歌而好词。至宋,“踏青药市之集尤甚,(俗)好歌曲”。这样,端公神婆们便吸取民间歌谣里的一些小调,出奇使怪,变化旋律,使其更适合于悦神娱人的演需要。大约初清以后,随着地方戏曲的崛起,端公和神婆也受影响,使“神歌”的内容从民谣杂语推进到宣扬因果报应,再推进到编演男女情爱和家庭纠纷的故事。于是也就出现了《女贤良》、《姊妹吵架》、《祖师成圣》等节目。
当时在陕南对“坛戏”有较大影响的是大筒子戏,本是秦巴山区社火秧歌发展起来的,端公为了招徕生意便邀集了一些民间艺人,特别是大筒子戏艺人为其“庆坛”踏歌伴奏陪唱,于是逐渐引进了大筒子戏的音乐唱腔与部分剧目,由于筒子戏的被吸收,使“庆坛”活动于端公戏迅速发展起来,乾隆时,在汉中、安康的丘陵、山区已有很大势力,连农民起义军也请其演唱。在此期间,端公戏又逐渐地吸收了秦巴山区丰富的山歌民谣与民间舞蹈的滋养,从而淘汰了原始宗教仪式中的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祈节目,也很少见宗教色彩,基本是健康的情歌与山歌。于是出现了许多以艺为业而非以巫为生的职业艺人与职业班,经常在汉水流域巡回演出,使端公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相传,端公戏有剧本200多个,现保存剧目120个。它的特点是:小戏多,喜剧多,表现下层人民生活的戏多,戏剧情节简单,矛盾纽结单一。汉水上游的端公戏,较多地接收了本地山歌和桄桄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派,称汉中派。它以汉中为中心,从汉水分界,汉水南路较多地接受巴山语音与二黄戏的影响,演唱风格比较柔和、细腻、辛辣、风趣、汉水北路较多地接受秦岭山区语音和桄桄的影响,演唱风格比较粗犷、悲壮、豪情激荡。
一
据称:荆山北麓一带,即今天湖北南漳、谷城、保康一带流传的端公舞,是由先秦巫教祭神歌舞演变而来,带有楚国巫风余绪,似有屈原《九歌》的史影。《谷城县端公舞源流初探》(以下称《谷》文)认为:《九歌》与端公祭山神……有两点是相同的:“其一,他们两者都是祭神的乐舞;其二,他们都是九段体的乐舞。”
《谷》文从民俗学的角度探索先秦文化是可贵的,但两点中第二点缺乏可比性,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北卷(下称《民舞集成湖北卷》)公布的材料,证明所谓“九段体”只能针对谷城一地而言,鄂西北其他地方的端公舞并非九场。而第一点也不能证明《九歌》与端公舞的关系,因为,传统民俗乐舞许多都以祭神为主要内容,如湘西、黔东的“祭傩神”、“吃猪”、“椎牛”;鄂西的“还大牛愿”等,非端公舞一例。
不过,《谷》文将《九歌》与端公舞比较,只是对先秦文化与现代民俗的关系,作了一种可能的推测,并没有贸然断言两者的历史渊源。然而,90年代初端公舞影响逐渐扩大,尤其荆山腹地残存的端公舞,其声名已波及海内外,大陆、台湾及日本、美国某些媒体深入荆山采访并相继宣传。媒体的效应不可低估,以至2004年襄樊“人大”讨论,拟将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公舞形成如此隆盛的局面有一个主要原因:十数年来地方政府与贤达几乎认同,“这一历史悠久的民俗舞蹈,是从楚国流传下来的祭祀舞蹈,是灿烂楚文化精髓篇章之一”④。显然,对于历史学和文学研究来说,现存的民俗能与两千多年前的《九歌》相联系,是极富魅力的,由此,端公舞可以成为研究《九歌》的宝贵材料,是先秦文学的活化石。
端公舞在鄂西北的不同地区有不同叫法,南漳叫“扛神”,谷城称“喜神”,保康谓“跳神”。各地场次有多有少,舞姿也不大一样,但主旨都是为求吉祥、兴旺、发财而娱神。过去往往在节庆、农闲或农家盖房上梁时,端公应村民要求而扛神,村民期望通过扛神获得诸神关照,求得吉运,广开财路。端公则因此得到村民的金钱或物质报酬。
扛神规模有大小,大的十几人,或者二十几人,在室外表演;小的三五人,在室内进行。乐器一般有鼓、锣、钹、镲等。除了主坛需要一件黄色长衫和黑色的腰带外,其他端公一律着蓝色长衫。
简陋古朴是端公舞的突出一点,不论视觉还是听觉方面的民俗元素,大致体现了鲜活的原状貌,这与当地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偏于一隅的地理位置相吻合。例如一种类似瘸子行路的奇怪舞步,即《民舞集成湖北卷》中所谓“颠颤步”、“颤点步”,《谷》文说是古代的“禹跳”流传到今天的“禹步”——大禹因治水染上风寒而行跛,后人为歌颂他的功绩,让巫觋摹拟了他的步态。
二
大型传统民俗往往会残留历史的痕迹,但是,端公舞是先秦楚地的遗俗,抑或说是《九歌》的孑遗吗?
综合各种看法,持此说的根据大体如下:一是有历史文献为证。《汉书·地理志》谓楚俗“信巫鬼,重淫祀”。鄂西一带为楚国始兴之地,由于地理偏远,楚人崇巫习俗得以保留下来,端公舞是为例。二是端公舞与《九歌》都是祭神歌舞,开场都要请神,终场都要送神。三是端公舞与《九歌》篇章结构一致,都是九段体的乐舞。
在现代民俗中能找到先秦文化的孑遗,令人振奋,但上述根据经不住初步检验,故笔者提出疑问并陈述粗浅看法。
首先,屈原《九歌》作于何地是个须考虑的问题。王逸《楚辞章句》谓《九歌》作于“沅湘之间”。朱熹认同:“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赞成这一意见的还有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鄂西北、豫西南与沅湘之间相距甚远,我们很难想象两千多年前的湘中民俗,竟然于二十几个世纪后在鄂西北表现出来。不过关于屈原《九歌》作于何地还另有看法: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九歌》作于汉北,即鄂西北豫西南一带,此为楚国始兴之地。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九歌》系屈原居郢都时作。当时的郢都即栽郢,栽郢距鄂西北不太远。郭沫若《屈原研究》则认为《九歌》作于屈原早年得志之时,屈原早年生活在郢都,《九歌》当作在栽郢一带。可见《九歌》作于何地,三者意见相近。陈子展还进一步认为:《九歌》“当为受命于怀王而作,即为楚国王室举行隆重的祀典而作。这是模仿楚之巫音的作品”。
王、陈、郭氏的意见,看来似可证明先秦《九歌》与今天端公舞在地域及社会风气方面存在的关系,但问题不可能如此简单,起码在民俗的演变规律上,其推论不能成立。
鄂西北固然是先秦楚国始兴之地,但由此将该地民俗径直上溯两千多年,打上楚的烙印,似乎有刻舟求剑之嫌。历史不是停滞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群不是永久固定居住,而是在历史中不断流动迁徙的,民俗也因自身的变异性,或者改变外在的形态,或者改变内在性质,或者消亡。
魏晋时期,今襄阳一带由于战乱,人口流动极大,本地旧族或者在兵祸中“一宗都尽”,或者举族避难南迁。此地若一时成为“空白”,即为北来流民聚散之地。北来人口之众,致使古襄阳之侨雍州成为当时湖北最大,人口最多的侨置机构。而无论南北来往,魏晋时期人口迁徙的规模和组织形式,都是以宗族和乡里为基础,以大姓豪强为主导的群体的流民迁徙活动,影响甚广,人口甚众。
由于襄阳地区为经纬冲要,魏晋时期人群变动剧烈频繁,后世凡逢战乱均无例外。所以,即或沔中即襄樊地区确存有尚无流动的所谓上古民俗,在迁徙浪潮的荡涤下,也不可能保存两千多年前的“原汁原味的……风采”。
无论哪个民族的习俗,在两千多年中都会发生变异与转移,都有消亡与新生的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各支系不断交融,今鄂西北文化面貌已去先秦远矣,故而将端公舞与《九歌》相联系,应考虑历史的流变性。同治《黄陂县志》第一卷“风俗”谓:“元末流贼之扰至明初,而土着者多迁四川,所有江右迁来之家,又或各自为俗,是风俗固难概论也”。清末尚且如此,何况站在现代的坐标上来追寻先秦的习俗呢?显而易见,民俗土壤不存,难有《楚辞·九歌》之“活化石”。
需要指出,今安徽中部与陕西汉中都有演出端公舞以求吉祥的民俗,可知端公舞不为鄂西专有。既然如此,“楚国始兴之地”所强调的传统在一地的延续性则不复存在。再者,《汉书》谓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楚人并不滥祭,杨华先生考辨包山、望山、天星观、新蔡楚简指出:楚人祖祭礼制总体框架接近周礼,别于殷制,之所以被班固斥为“淫祀”,是因为它不如周礼严格细密,存在“非其所祭而祭之”的内容⑨。可知,楚人“淫祀”只是程度和范围的问题,与列国并无性质上的区别。况且他国也有淫祀的现象,如鲁国“季平子祷于炀公”且立宫⑩,分明也是“淫祀”。杨华先生指出:过头、过分的祭祀在先秦不乏记载。据已知材料,当时宋人、秦人、越人的巫教观念及崇巫的热情不亚于楚人,所以,班固谓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特殊性还需具体分析,不宜简单理解。
芦山庆坛有完整的演出程序。由九部分组成:
1、开坛(含灵官镇坛);2、放兵; 3、出土地(此折最多可演七出折子戏);4、请神;5、出倮倮;6、童子请仙娘:7、出二郎(或叫“二郎记”或“二郎降孽龙”):8、踩九州;9、收兵札坛(含灵官扫坛)。
这套程序中,其中1、2、4、8纯系法事仪式,而3、5、6、7、9为有人物、情节,歌舞说唱并重的折子戏。同时,庆坛还有“一折灯一折坛”的习俗。在庆坛程序中,随时可以插演民间灯戏或歌舞小剧。这是,一为顾及主家和观众祈神与观赏的需要。在请神、酬神的同时演出部份民间小戏,达到娱神娱人的双重目的;二为适应庆坛时间的需求。一般庆坛一至三天,大坛时间有的长达七天。小坛演出既定程序即可。若庆坛时问长,则要插演更多的娱人剧目,以适应坛事。
芦山庆坛经常插演的剧目有《请长年》、《裁缝偷布》、《安安送米》、《九流相公》、《张浪子薅豆子》以及对花名、盘歌、数麻雀等歌舞小戏。
芦山庆坛的唱腔,主要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为“端公调”或叫“神歌腔”,用于开坛,请神等法事仪式。第二部份“胖简筒腔”,用于娱人的灯戏节目。最后一部份是民歌小调,用于花灯、歌舞类演出节目。法事仪式,由锣鼓做节拍伴奏,演出灯戏,小剧目,采用花灯锣鼓或川剧乐队伴奏。
附 艾子的天空 美文一篇
穿越黑暗的歌与舞
从屈子先生的《招魂》里立起来,走出来,从楚郢都豪华的宫殿里飘出来,隐下来,到今天,“端公舞”和“巫音”这对爱侣,已经2000多岁了。 2000多年来, 他们忍过中原文化对它们的呵斥和白眼儿, 躲过政治对他们的撞击和杀伐, 悄悄隐藏在荆山山脉的皱褶里,存活在荆山山民大喜或大悲的日子里。这就让人的内心充满了感动——养育了800年楚国的荆山,象所有伟大的母亲一样,悄悄收藏起大富大贵后又惨遭不幸的儿子的遗物,泪水擦干,表情平静,内心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儿子走了,孙子一定要带大!自家的这只血脉一定要延续下来。
一
恍兮惚兮,时光倒流。3000多年前,在森林密布的沮漳河流域,走来了一群蓬头垢面、赤胸裸足的“蛮夷”。这是历经数次劫难后侥幸活下来的芈姓季连的族人。殷商集团的暴政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他们被“统治者”追逐得东奔西窜,千里辗转,一路逃亡。这一天,他们来到了荆山脚下。这是一块肥美的土地:树木荫天敝日,河水丰沛清冽;肥壮的动物四处游荡,茂密的荆条摇曳多姿。脚下,是油黑的土地;头上,是瓦蓝的天空。饿了,满山的果子随意采摘;渴了,弯腰就是甘甜的泉水。这是一块这么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是上天赐给逃难人的礼物,那么,就住下来吧!开始稼樯伐猎吧!
恍兮惚兮,日月飞驰。稼樯伐猎的部落长大了,它饮马黄河逐鹿中原了。青铜器、刺绣、丝织品、漆器……随着凤鸟的飞翔傲视着四方,至今还在考古现场刺激着人的感官。“蛮夷”的天更蓝了,云更白了,地更大了,兵更强了,马更壮了,食物更丰盛了,器皿更精美了,服饰更考究了。余下的时间,他们在细细打理精神世界的食粮。那里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最重要的是,那里有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
渊源实则更早。丰饶的荆山沮水养育了婴幼儿时期的楚国,所以楚人的情感,离自然近,离礼法远。颠沛流离之际,“以启山林”之初,面对变幻无常的造化,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惊惧。他们用惶恐的眼睛打量着世界,忽然发现,原来每一个现象的后面,都有一个神灵在左右:日神、火神、河神、云神、山神……。这些神灵悄无声息地站在楚人的身后,忽隐忽现。你看不到他,他却在考验你,处罚你或庇护你。于是祈求和感恩,成了楚人舞蹈的原生意义。两人相对,翩翩起舞,是为“巫”字。它成为楚人精神生活的第一娱乐,连最伟大的诗人也陶醉其间,用优美的篇章描述了让人心旌荡漾的场景。因于此,你可以说,对神灵的崇拜已经幻化为一种物质,渗入到楚人的血液里,并随着血液一起流淌,代代相传。听吧,楚舞翩翩,楚音幽幽,“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庭震惊,发激楚些。”古朴的乐器奏响出神秘的音乐,这是楚人在宁静的心境中找到的与大自然相契合的途径。优美的舞蹈“偃蹇”“连蜷”,这是楚人在长袖轻拂中弯下腰去恭敬地迎接天神的降临。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在北方人的眼里,楚人是那样的耽于享乐,以至于多年之后他们酸不溜溜地总结出“楚之衰也,为作巫音;齐之衰也,为作大吕”这句话放在《吕氏春秋》里来训喻后人。他们抨击这种取名“巫风”的音乐舞蹈,说它直接助长男女蝶亵的淫风,是亡国的征兆。并笑话那位楚灵王在“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兵临城下的危难时分,还“鼓舞自若”,因未完成对神灵的祈求而不与迎战。失败者永远没有话语权!我想说的是,秦国的修史官哪里敢直言楚人沉醉于浪漫歌舞中的愉悦呢?
二
你看,当这个充满神秘、诡谲气质的男人开始舞动时,他的妻子“巫音”,便也在一旁深情地伴奏了——
穿一件黑色长袍,戴一个纸做的五佛冠帽子,持纸糊“钺斧刀八卦旗”等法器,在阵阵“呜呜”作响的巫音催促下,在人们长久的企盼中,端公师飘然上场了。“五佛”端坐于纸上莲花台,“钺斧刀”则直接抵达夏商两朝最高权力,这暗喻着表演者曾经血统高贵,也昭示了端公师可以上通神界下达人间的特殊身份。是的,从鬻熊到熊绎,几代酋长都是大巫,大诗人屈子也曾为怀王招魂。是王公的喜好引领了时尚,决定了民风,致使楚国巫风弥漫,巫舞炽烈。只是它一路走来,2000多年的时间太过漫长,它早已丧失了庙堂之上的荣耀,只能栖息在村野之中,慢慢成为民间一种谋生和挣钱的手段。在今天的荆山深处,所有端公师的扮演者、巫音的演奏者都是农民,稍微能认几个字的农民。想到这里我就陷入了一种不解:古国源长,文明浩荡。但为什么往往是最卑微的农人在保存我们民族原始的记忆?充当着历史文化的传承人?为什么只在偏远闭塞的乡村保留着曾经灿烂的文化?是山高水远阻隔了外来文化对它的冲击?还是世人心中没有文化的农人对苍天、大地永远的敬畏象一层坚硬的外壳把它紧紧地裹在怀里?楚地山民对苍天、大地的敬畏就如同藏民对圣山圣湖的敬畏一样虔诚,在这看似愚昧的信仰里,其实包含了多少正确、和谐的朴素真理啊!
楚人的端公舞上祭祖先、下敬土地,同时敬奉众多神祗。翻开相关文献,你的眼前就会立即浮现出一幅幅“酣歌恒舞”的画面。那是几千个过往的十冬腊月,楚人择了一些吉祥的日子请端公师在歌舞,或还愿,或娱神。这种浪漫的习俗在时间的河流里缓缓流淌了2000年,基本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只是在近40年内,它迅速消瘦、老去,失去了它曾经青春的容颜和大部分内容,只剩下了“超度亡灵”这一个内容。
很小的时候,我曾经远远地见过端公舞,几十年后,我再次在二娘的葬礼上见到它。这时的我,已经成为一名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无比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我站在端公师的身后,想起幼年时广泛流传于家乡的一句话:“跟着端公杠假神”,心中就一阵阵地悲哀!一个民族原生态的文化竟被斥为毒草,几尽赶尽杀绝,整整模糊了几代人的视线,这该叫人怎样地仰天长叹、扼腕痛息、捶胸顿足都不能释怀?所以我如饥似渴地欣赏这养育了我的祖先的舞蹈,去倾听它来自远古的吟唱。
寒风彻骨,冷月高悬,二娘家的大门口挂满白色的纸条,红色经幡飘荡在高高的竹竿上,一种悲伤的气息在空气中缓缓流淌。灵堂前放置着二娘的遗像和供品,灵堂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布幔,上面画有元始天尊和两条蟠龙。也许经过岁月的烟熏火燎,也许承载了太多神灵、亡者的来来往往,布幔已发黄发暗。它的下面,是香案。上面放着法器、令牌等物。我仔细辨认令牌上的三个字,分别是雨字头下面加弘、登、盟,端公师也说不清它的意思,说是师父的师父都这样写的。
长号呜咽,端公师轻移脚步,开始他的“整场演出”了。他先是表情肃穆地立在香案前,恭恭敬敬地一个长揖,然后转向亡者遗像,边挥舞着手中的法器,边开始低沉地吟唱。半个小时后,端公师放下法器,离开灵桌,用一种轻轻跳跃的步姿,围着棺木一圈一圈地绕行。这是极其讲究、极有法度的步伐,由一代代端公师口授心传,据说走错一步,就无法与神灵沟通。他的口中喃喃有词,有时会突然“讶!”地大叫一声,倏尔又恢复到伊始的平静。他的步姿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变化,开始大幅度的跳动。他的一条腿突然离地,高高地跃起,他的一只肩膀同时也高高耸起。我惊讶着他会不会失去平衡,跌到地上的瞬间,他的脚已落到地上,而另一侧的肩膀和脚已经快速地腾起。他就这样重复着两侧腿和肩的动作,交替着腾起、落下,再腾起、再落下……他的身后,是排成一列的孝子和晚辈亲属。他们披着曳地的白麻孝布,随在端公师的身后,踽踽绕行。绕上十几或几十圈后,端公师要停下来,换用溜冰一样轻捷盈捷的步姿,满灵堂疾走。口中依然喃喃有词,胳膊在不断地变换动作,忽高、忽低、伸直、蜷回、抱胸、向天。孝子们的队列不变,动作不停,累的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会有其他的亲属补进去继续。这叫“守夜”或“打丧鼓”——亡人的灵魂已被端公师从茫茫天界找回来,就附在遗体上、或落在灵堂的某个角落。这是与亲人的最后一夜相守,天微明时,她就会被天神带走。端公师边跳边掐算着时辰。他想着天上的神灵。他要接天界的神灵下来。我问端公师的一个徒弟:“神叫什么名字?”徒弟答道:“大司命”。一个没有文化的年轻山民竟然知道“大司命”,我心中一阵阵温暖。阳春白雪如《楚辞》在下里巴人处被记忆得如此完好,泪水先因了这,再因了永失二娘打湿了我的眼眶。
夜幕拉开,天将转明。端公师撇下了孝子,一人站在了灵桌前。对着亡者的遗像,他半闭着眼睛,敏捷地腾挪、移动,他在翩翩起舞了。他的动作轻巧、灵活,他的唱词更多时候语焉不详,象是一种喃喃自语。对天界的神来说,或者这是他们独有的语言系统。端公师沉醉在他将要达至的神界,它周围的气氛更是诡异了。他的丝质长袍在移动中轻轻抖动,一种神秘的气息便在这抖动中缓缓飘起。他的表情是谦恭的,步伐是轻巧的,声音是柔软的,但却有催人泪下的法力。他的眼神是迷离的,灵魂似乎已经出窍,正在九界上迎接飘然而至的神灵。所有的人都被他带到了这个境界。你看哪,神已缓缓下降了,它轻轻地靠近端公,对着他耳语,端公止住脚步,面色凝重地聆听着,口中继续喃喃有词。十来分钟后,神要飘离了,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我似乎看清了他的面容——方额长颈,明眸皓齿,穿着宽袍长袖的神衣,佩带着形形色色的宝玉,若隐若现,忽暗忽明。这是长久以来文献描绘给我的司命天神的形象!他的身后是我的二娘,一生辛苦、勤劳善良的二娘,她跟在神灵的身后,满脸痛苦的表情——她不愿意离去,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她会孤单寂寞。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天命不可能违抗。魂兮归来,转瞬即分,这一刻,巫音大作,端公跳起了更热烈的舞蹈,亲人们纷纷落泪。人们一起恭送着神灵的离去,希望神灵能够关照二娘在前往天界和投胎的路上少受苦难……
三
一个晚上的时间,巫音始终陪伴在端公师的身边。巫音班子中的长号手们吹出了凄凉、幽暗的第一声,然后镲、锣等一起响起,唢呐的哀怨呜咽,战鼓的原始粗犷,配合端公师神秘的舞蹈,感染着前来祭奠的每一个人。在她的深情伴奏下,一整夜的时间,端公师从未停止他的神秘吟唱。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歌曲呢?我有幸得到过几段唱词,读它,就是在读《山海经》的通俗版本:
孝家一副好棺木, 说起棺木有根古。 昆仑山上一棵树, 此树名叫长生木。 左边枝头凤做窝, 右边枝头老龙洞。 只有盘古神通大, 手执一把开山斧。 先天元年砍一斧, 先天二年砍半边, 先天三年才砍倒, 先天四年落凡间。 鲁班先师一句话, 先造死,后造生, 生生死死根连根, 万古千秋到如今。
这是怎样浪漫的唱词!想象丰富,意境遥远、平静、达观。或者有人会想:为什么不是哀伤的、让人泪水涟涟的唱词?在楚人的心中,星移斗转,沧海桑田,死亡的只是肉体,灵魂永远存在。灵魂离开躯体,有时是鬼,有时会升格为神,但更多的是投生——让生命重新开始。一个人老去,全村人来祭。沉沉黑夜中,场地上生起火堆,人们围着熊熊火堆击鼓赛歌,“伴灵”、“闹丧”,这与其说是对死者的悼念,不如说是对亡灵的欢送。在他们的心中,生命与宇宙诞生一样,从黑暗混沌中来,享受光明,老死后重归于混沌黑暗希冀再次新生。这是多么朴素的宇宙观、人生观,这是楚人精神最真实的吐露。正是缘于此,才有3000多年前楚人从奄奄待毙到霸临天下,才有庄子精神,也才有端公舞的绵延流长和巫音的声声不息。
端公舞的唱词中含有大量的信息,神话、历史、想象、现实……内容包罗万象。这些丰富的内容,滋养着楚地山民几千年的精神生活,由此我想到《黑暗传》。就是脱胎于我眼前这样的楚地祭祀活动,现仅存在于丧歌行列的这些歌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全国性的文化大普查中,在神农架地区被搜集整理。这本是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认为它是一块罕见的“文化璞玉”,极有可能是“汉民族最早的血脉和记忆”。虽然《黑暗传》是否能定位成“汉民族广义的神话史诗”,但它从神农架民间口头传唱的丧歌之列走向神圣高雅的学术殿堂已让楚人欣慰之至。这在一条充满艰难的传承路上,可不可说:一代代乡野山民是它最得力的文化义军呢? 有时候,我憎恨那些被称作“流行”的东西。它们太过霸道,疯狂地占领,挤走一切,哪怕是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厚重文化。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化会沉淀下来,也会延续下去。而且每经历一代人,就会涤除一些尘滓,就象端公、巫音、黑暗传,走到今天,剩下的是直面生死、达观平静而又温情脉脉的歌舞。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 上一篇: 解读什么是谶纬神学?
- 下一篇: 为什么鲁班书不能看?
热门标签
星座查询
情侣速配
性格解读
最新更新